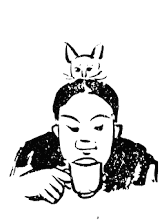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转载自《南方周末》)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 张鸣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 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 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 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 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 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中国的耻辱,人民都很愤怒等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革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战胜其实是兴奋的。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动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ht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 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 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 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 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 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 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