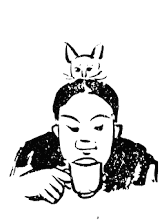〈论华人之可用〉
这一篇〈论华人之可用〉,见于郑振铎先生编的《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初版),放在严复的名下。1962年,中华书局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一部《严复集》。经过考证,编纂者对于此篇是否为严复所作提出质疑,所以没有收入1962年的《严复集》中。1962年的质疑与1937年郑振铎先生的收录,各有其见解。对于2008年的我来说,无论该文作者是不是严复,他的口吻和从中透出的阅历,与严复实在很像。
此文互联网上还见不到。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从《晚清文选》中把这篇〈论华人之可用〉敲录下来,为网络上的人文资源添一块砖。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始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其间者,或理账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暧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以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赡,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消,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驰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而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