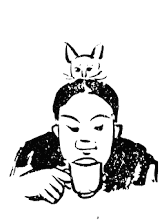西塞罗的愤怒(转载)
西塞罗的愤怒——评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
高峰枫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 BC - 43 BC)是古罗马一代文宗,其著作涉及面极广,既有打官司的讼词,也有哲学、政治学和宗教领域的著述,更不要说彼得拉克在1345年发现的那几百封书信了。 若对古罗马文史缺乏了解,对西塞罗雕琢、繁复的文风没有体会,那么翻译(translate)西塞罗很容易成为对他的“侵害”(transgress)。 买到汉译本《西塞罗全集》第一卷《修辞学卷》时,我便替译者捏一把汗,待看了译文之后,我早已被惊出好几身的冷汗了。
译者翻译所用底本,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他沿用英译本的做法,把Ad Herennium(译者翻作《论公共演讲的理论》)列为第一篇。译者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否西塞罗本人的作品在西方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可是据我所知,“主导性的意见”刚好相反。据考证,Ad Herennium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初期,是现存拉丁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修辞学的系统论著。在中世纪以前,这部书的抄本大多将西塞罗题为作者。但是自十五世纪开始,人文主义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便开始质疑西塞罗是否真的是此书作者,并且当时已有其他学者将此书排除在西塞罗作品之外。这样一代代研究考证下来,只要您随便翻阅几部研究古罗马修辞学的著作,从英国学者Atkins的《古代文学批评》第二卷(1934年),到加拿大学者Grube的《希腊罗马批评家》(1965年),再到意大利学者Conte的《拉丁文学史》(英译本1994年)和美国学者George Kennedy的《古典修辞学史新编》(1994年),没有一位将这部书归在西塞罗名下。译者也许无暇翻阅这些基本参考书,可是就在他依据的“洛布古典丛书”英译本中,英译者Caplan在英译者序里明明说过“虽然以西塞罗为作者的观点仍不时出现,但近来所有的编校者均以此说为谬”,“此书作者问题不时引起学者讨论,但从未获得最终解决,也从未让所有人满意。我以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将此书归于一佚名作家笔下……”译者只要认真看过这篇英译者序的前三页, 我想他绝对不会说出“但主导性的意见仍视之为西塞罗的著作”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西方古典修辞学有很多基本术语。比如按照“演说”(oratory)的主题和功能,一般将“演说辞”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庭议”(deliberative),专门讨论军国大事,比如宣战、媾和、立法等等;第二类是“诉讼”(judicial或forensic),用于在法庭上控告他人,或者为当事人辩护。第三类是“赞咏 ”(epideictic),服务于讴歌君主和颂扬英烈。当西塞罗将这三个修辞学基本术语放在一起讨论时,译者尚能知其差别,勉强翻出大意。而一旦它们在文章中“落单”,译者一下子就双目迷离,辨认不出了。比如第150页,forensic单独出现了,身边没有deliberative和 epideictic“相伴”,译者忘记其义当为“诉讼”,三次将它译成“辩论性”。又如第170页,出现了一个deliberative style,这本来是议论国事所应使用的文体,而译者却译作“演讲术的精致文风”,估计是将deliberative往deliberate(深思熟虑) 的方向上理解去了。对修辞学基本术语不熟悉、不敏感,却勇于翻译古罗马修辞学巨擘的鸿文,正好比不懂悲剧和史诗的基本差别,就胆敢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
古罗马文化根深叶茂,特富于宗教精神。不了解古罗马宗教的情况,就不容易看懂当时的书籍。西塞罗在《论开题》(De Inventione,我暂不谈这个题目译得是否准确)第一卷中说,若有人偷盗“祭器”(原文sacrum,英译sacred article),那么他到底是犯了盗窃罪呢,还是犯了渎神罪?他提到的“祭器”,本来是指用于宗教祭祀、具有神圣性的器物。可是,译者却别出心裁,把“ 祭器”译作“圣书”(149页)。真是神来之笔!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译者对古罗马宗教缺乏基本了解,请问古代罗马人是希伯来人那样的“圣书的民族” 吗?第二、译者对article一词的理解,似仍停留在中学阶段。在他的心中,这个词只可以表示“文章”,不能表示“物事”和“器物”。
这部九百余页的译作,只要你随便翻出一页来核对,便会发觉满目疮痍。任何译者偶有疏失,本来在所难免,但是满篇讹谬,而且都是最最基本的英文理解问题,这就让人大大怀疑译者的语言能力。我随便举些例子,大家可自行判断。
先说单词。拿《论开题》一篇来说,仅开篇的前十页(141-150页),至少就有六十多处误译和漏译。如果更较真一些,可以轻易突破一百大关。短短三页之内,一个简单寻常的英文单词agreeable居然出现三种译法。在第142页,译者将agreeable译作“已经同意的”,把同页下一段出现的 agreeableness译作“赞同”。而在第144页,又将agreeable译为“统一”,真不知和前面的译法如何“统一”。译者大概以为 agreeable是agree和able两词的简单相加。可是,只要随便翻翻字典,就会发现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令人愉悦”、“宜人”,而西塞罗文章中这三处的拉丁原文(iucundissima, commoditas, iucunda)也都是“愉悦”或“合宜”的意思。至于把“分配”(assign)翻成“确定”,把“同意”(approve)误作improve而翻成 “改进”,不懂双重否定而把not inconsiderable译作“不太重要”(意思满拧了),也都可以在这十页之内发现。
如果我们越过遍体鳞伤的前十页,看看《论开题》其他部分的翻译,不仅可以找到很多漏译(英译本第97页整整十八行在汉译本第175页上面突然“人间蒸发”),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译者对一些常见英文单词和词组的“独特解会”:rigorous(严格)如今有了“生动”的意思,in a position to do(有权作某事)已可表示“在事发现场”,“愤怒”(indignation)已然生出“尊严”,而“侮辱”(insult)已经造成“结果”(第 171页,196-197页)。按照译者对英语词汇学的这些最新贡献,我劝他能够接受更“生动”的学术训练,千万不要“结果”了读者的智力。
《论开题》的后面,是一篇小品《论最好的演说家》。这篇小品应该算是最容易翻译的,但对于译者来说,又成了他的一处滑铁卢(又有哪一页不是呢)。在不到九页的篇幅里,我找到四十余处错误。最让人长见识的,是“审判官”(referee,拉丁原文作iudex)被译者置换为“证人”。由证人来审案,这样的法律改革不仅时尚,而且大胆。考虑到译者在前面“屡译屡错”,只好满心希望他的英文水平在后面能够有所提高。可是,译者并未如我预期的那样“蛇头虎尾”,按照最保守的统计,他的出错率还稳中有升。前面说过,《论开题》前十页错六十余处,不足九页的《论最好的演说家》错四十余处,到了全书倒数第二篇《布鲁图》(Brutus,西塞罗晚期作品,评论在他之前诸大演说家,略同于一部古罗马修辞学简史),仅仅前二十页中(第658-677页),至少已有两百余处误译和漏译,创下每页接近十个错误的新高。我只举几个最有创意的例子:“闲适”(ease)两次被译成“停止”,“回忆”(recall)被译成“召唤 ”,“不无骄傲”(not without arrogance)变成“无知”(看来双重否定永远是这位译者的软肋),“哀叹”(deplore)变成“探索”,“贬低”(belittle)变成“ 缩小”。按照译者的“翻译逻辑”,既然belittle是“缩小”,那么belong想必就该是“拉长”了!这样的的英文水平,真值得我们“探索 ”(deplore)!
再说文法。在《布鲁图》里,布鲁图希望西塞罗谈谈对恺撒的看法,言语上不必有所顾忌。恺撒不仅是一代枭雄,而且他无碍的辩才足可与西塞罗比肩,他作为演说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可能避而不谈,这是因为(以下是正确的译法)“你对于他才能的评骘,尽人皆知;而他对你的评价也不是什么秘密”(your judgment about his genius is perfectly well known, and his concerning you is not obscure)。这句英文除后半句有所省略之外,实在没有什么难懂之处,但就是这样简单至极的句子,到了译者笔下,却摇身一变,变成匪夷所思的一句谜语:“他确实像你所判断的那样是一个天才,十分完美,非常出名,你清楚地知道他关注什么”(第740页)。英文系本科新生都知道perfectly是副词,concerning是介词,这种“小儿科”的句子译者居然也不会译。唯一让我欢喜踊跃的,是agreeable一词在第672页终于译对了(“一位招人喜爱的演讲者”)!但是译者经过五百多页的长途跋涉,方才弄懂这个词的意思,用双重否定来说,代价不可谓不高!
译者自称“愿意耗费几年的时间译出西塞罗全部现存著作”。这样大的愿力和魄力着实令人钦佩,但他是否对自己的学术功底和语言能力有些估计过高了呢?译者此前已经拿他的译文惹恼过炼狱中的柏拉图和天堂里的圣奥古斯丁(他曾独力翻译过《柏拉图全集》和《上帝之城》),这次准备要拿西塞罗“牛刀小试”了。但我真怕西塞罗的亡魂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不安地从炼狱中升起,使出他修辞学作品中提到的挑动公众和陪审团“义愤”(indignatio)的十五种“激怒法”,把译者和出版社一起告上学问的法庭!
来源:东方早报2007年8月2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