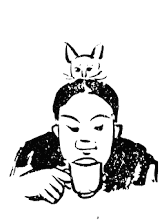被燎掉的大胡子(转载)
被燎掉的大胡子
张鸣(《读书》杂志,1999年6月)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就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訢领衔,直隶总督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十七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价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把事给搅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父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崇,不如请神父来念经驱邪。 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国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那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父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造,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 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洞,其实并不严重。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 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汪县令不知道,就是这几个嘴巴,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 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划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祛邪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在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德、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是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 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的推荐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土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村事务事事干预;一是天主教的进入,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 起走乡绅们走过的科场之路,关键是两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村固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由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的关联的一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学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可以想像,在些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可能一个局部的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的多一点,是气总要出一点,逢着民教冲突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的武力的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 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子依“ 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决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时,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纷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由于遏制政策的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的在文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琢磨才是。